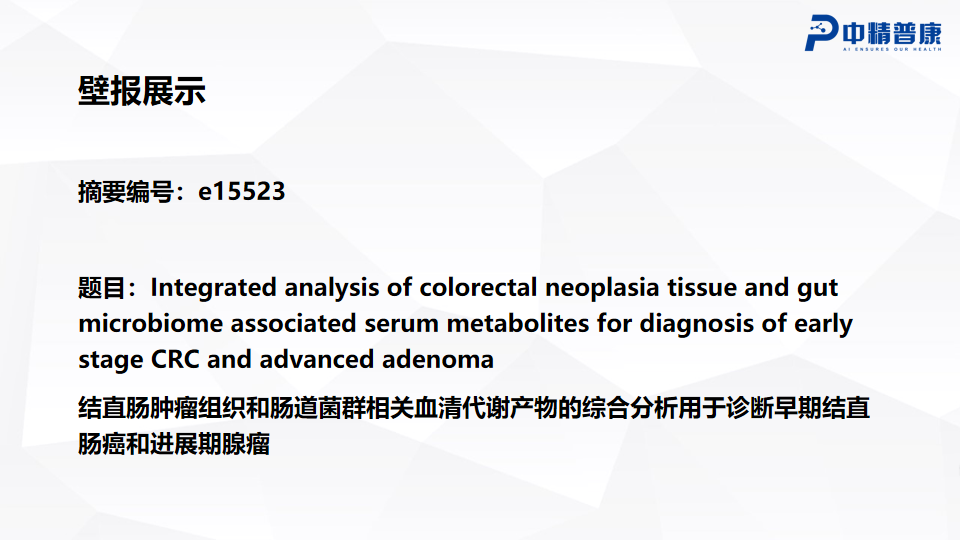音乐剧《赵氏孤儿》对戏剧的现代告白
对戏剧的现代告白
近期,音乐剧《赵氏孤儿》在上海热演,好评如潮。它不仅代表了华语音乐剧新一波浪潮,也让观众再次看到,中国戏剧丰沛的文化意象和磅礴的精神力量。导演徐俊花费三年时间打磨此剧,在此期间他始终目标坚定。当首演的灯光亮起、乐声乍响,他意识到,自己完成了一次对中国戏剧的“真情告白”。
作为第一部传入西方世界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被公认为“全人类戏剧中的不朽之作”,其正义战胜邪恶、崇高睥睨卑劣的主题,以及被命运车轮碾轧的平民形象,始终有着未曾黯淡的光芒。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流变和跨国界传播中,中外戏剧家以不同的眼光去解读其独特的价值,围绕戏剧核心的聚焦与修正、强化与弱化,赋予了这部伟大剧作不同视域下的生命能量。
2012年,英文版话剧《赵氏孤儿》在莎士比亚的故乡上演。五年后,徐俊导演接触到了这部出自英国诗人詹姆斯·芬顿之手的《赵氏孤儿》,为之兴奋。从中,他看到这部中国戏剧蕴含的超乎想象的开放性,也看到了现代文本破解其核心困境的可能性。他决定在英文版话剧基础上,创作华语音乐剧《赵氏孤儿》。
在创作过程中,徐俊导演希冀尽可能多地保全芬顿剧本所呈现的现代视野,更期待通过音乐剧形式使这些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未来舞台上构筑起一个强大的情感磁场,给当代观众一个足以让他们倾心热爱的理由。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在戏剧结构、价值旨归、诗性特征、音乐语言、视觉方向等方面进行了艰苦而理智的选择,并愈发清醒地认识到,音乐剧相较于其他艺术样式,更需要文学的锤炼、音乐的浇灌和舞台的锻造,而其中蕴含着无限的创造力。
对人物的真实刻画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部音乐剧《赵氏孤儿》分为两幕。两幕戏分别设有九个场次,在整体结构上显得十分规整。这一布局,同时也很好地均衡了“前因”和“后果”这两个叙事要素。在一些古老版本中,习惯将叙事焦点投注于“前因”,即“救孤”,对“后果”的铺陈则相对粗疏,这就使主题的呈现受到一定局限,悲剧性也未能在更深层面得以展开。戏剧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有头、有身、有尾的逻辑整体,是对一个行动完整的追述和模仿。这一次的音乐剧改编,更注重“救孤”之后的戏剧走向,着意于揭示情节的推动关系和必然结果,其中,人的意志行为作为逻辑主体得到了充分的张扬和完整的表达,这也是现代文本有别于古老版本之所在。
音乐剧《赵氏孤儿》的第一幕仍可标注为“程婴救孤”,它是故事的发端、两大核心事件之一。英语版话剧以五个场次的篇幅来铺垫“灭门”事件的起因。而在音乐剧改编中,对这部分情节作了大幅度削减。舞台上以三个平行空间交代了颇为复杂的背景,并通过一首合唱和对唱,完成了首个戏剧冲突。这一洗练的处理,为深度开掘主人公内心世界留出了大量的叙事空间。
程婴的内心在第一幕可用“选择”两个字来概括:禁军统领屠岸贾大开杀戒,程婴踩着尸体蒙召入宫,为公主接生,他清楚自己身处险境,但没有退路。当公主将赵氏孤儿托付于程婴时,程婴几乎被吓破了胆。之后,程婴继续在命运漩涡里翻滚,他之所以接受公主的托孤之请,选择了担当,对于这一转变,文本从多侧面作了精准的描写,而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是,襁褓里突然传出咿呀之声,震痛了程婴。看着婴儿如同求救的眼神,程婴唱道:“此刻我怀抱着赵氏孤儿,他就像我那刚出生的孩子。”至此,我们清晰地看到,是父爱的本能,是内心善良的微光,让程婴作出了救孤的选择。
一介草泽郎中,也许他内心没有足够的土壤来培植“崇高”这棵大树,在他身上只有人最基本的善良;他能理解的是,杀戮是恶,拯救弱小的生命是善。程婴被内心善良的微光所照亮,很快,微光也灼痛了他的灵魂。这是刻画程婴这一人物最为精妙也最为准确的一笔。
一个真实的戏剧人物,不是某种假想模板的图解,更不能用既定的道德框架去框定他。他所拥有的丰富性和真实性是整个戏剧坚实的基础。救孤后程婴的种种选择,应当说,同样受到了事态发展的巨大推动。与其说是程婴选择了大义,不如说是命运选择了程婴,而他始终是那个被命运车轮一次次碾轧的布衣草民。随着剧情发展,身边的忠臣义士一个个死去,“杀戮与拯救”以殊死的姿态,在程婴面前突然被放大。在“善良被插上刀尖”的一刻,程婴终于发出了“善良从未荒凉,我会像熊熊大火一样”的呐喊。在命运的裹挟下他一步步被推上道德的制高点,心中的微光已然升腾燃烧,以至于酝酿出一场“复仇”的风云大戏。在这一点上,音乐剧《赵氏孤儿》做得全神贯注,不遗余力,不惜留出大量的篇幅来推动这种人物进阶和戏剧性发展。当程婴完成重要唱段《绝不可以》,余音回荡中,一个丰满可信的形象已经站立起来,且经受住了观众挑剔的眼光。
对改编的大胆突破
第二幕以一首《复仇之路》拉开帷幕。紧接着,程婴、屠岸贾、赵氏孤儿的重唱《我已长大》从不同角度叙述了十六年的时光流转,交代了人物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复杂心态。
在这里有必要提一提作词人梁芒为这部剧贡献的歌词——歌词智慧地融合了叙事与抒情两大要素,这在一般的音乐戏剧中是一个需要花大力气去解决的技术性难题。在这部剧里,观众经常可以看到,是丰富的文学想象带动着情节、情绪的展开,唯美而实用。所谓“实用”,主要是指它传递给观众的信息是丰富、多元的,同时又是深入的和直抵人心的。它不仅为全剧形成独特的风格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作品的文学品格置于一个很高的位置,充分显示了音乐戏剧的魅力。
再谈第二幕两处重要的改编:进入“舞象之年”的赵氏孤儿,被程婴安排了一次远游,理由是“采集药草,历练意志”。在以往的古老版本中均没有“游历”的情节,作为芬顿剧本的重要增设,它为复仇的合理性作了关键性铺垫。在音乐剧改编时这一作用则被进一步放大:走出宫门的赵氏孤儿看见了真实的世界,也目睹了在“养父”屠岸贾的暴政下民不聊生的严酷现实,少年震惊了,他激昂地唱道:“现实像一杯毒酒,为何被描绘得那么可口?”此时的赵氏孤儿不再是受命运驱使的复仇者,他内心有了一份作为人的责任。当他了解了自己的身世后,家族的仇恨已然溶解在为苦难苍生、刀下冤魂讨还血债的宏愿之中。这也是程婴复仇计划中的一步。程婴清醒地意识到,赵氏孤儿作为一个有独立意志和个人情感的人,面对恶贯满盈的养父,有权利作出无愧于心、不惑于情的自由选择。他安排赵氏孤儿远游,让他结识守边将领魏绛,都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这一笔对程婴的人格描摹是十分有效的。当赵氏孤儿用猎刀刺向屠岸贾时,程婴相信,这是一个长大成人的男子汉代表正义所作出的选择。将狭隘的复仇意志置于一个宏大的背景下,这样一种改编,显示了现代视野对古老文本的朗照,它带给现代观众的不只是惊喜,更是一种情理上的认同。
全剧将近尾声,“亲子该不该献出”“养父该不该手刃”两大古老的伦理质疑,在这样一次当代改编中,智慧而不动声色地得到了合理解决。然而,当代观众对故事的完整性有着更深层次的追求,剧终前的一刻,人们更关心程婴这一人物的精神归宿。程婴的儿子无辜丧命,他是随着父亲的选择,“祭献”给了崇高和善良。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他没有选择生死的权利,甚至没有发声的机会,在所有的古老版本中他都作为一个道具而存在,被忽略了一个生命个体的尊严,而这在当代观众心里是一个过不去的坎。作为剧中人物程婴又何尝能跨过这个坎?如何让程婴与自己的心灵达成和解,对当代改编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芬顿以理性的反思和诗性的火花,创造了“程子”这样一个角色,并让他在全剧的最后,以赵氏孤儿同样的少年形象出现在舞台上,与父亲作灵魂的对话——此为第二处重要改编。徐俊导演则进一步推动并强化了这种现代性表达,他让“程子”成为一个贯穿全剧的人物,有一双洞悉世象的眼睛,让他亲眼看到风云变幻,光明被黑暗遮蔽,爱跌入恨的泥淖;让他站在父亲身边去体味痛苦、孤独和煎熬;让他依偎着母亲聆听那首绝望如悲鸣的《摇篮曲》;让他一次次与赵氏孤儿对视,从“替他活着”的那个少年的眼里,看到了两个人的生命,两个人的力量。三首重量级曲子完成了这一角色的整体构造,同时将俯视和直观的两重视角作了有机勾连。这一角色的创造,是音乐剧《赵氏孤儿》最为精彩、也是最闪亮的一笔,其背后是大胆突破和有效激活的艺术理念。
程婴完成了使命,来到荒野,寻找儿子的小小孤坟。在坟茔前,父子实现了一次跨时空的对话。程子悲愤地诘问:“父亲,我到底犯了何错,你把所有的爱给了另外的孩子?”面对无解的生命疑问,程婴选择的回答是:“把你冰凉的手放在我衣袍的褶皱里。”他希望用身躯去温暖冰凉的坟茔;希望“打开我的胸膛”,让爱子“住进我的心脏”;希望父亲的血与儿子的流淌在一起。当委屈了十六年的儿子向他索讨爱时,他唯一能给的只有已然破碎的“父爱”,他愿意全部献出。我想,这是程婴给自己也是给当代观众的“一个没有遗憾的答案”。全剧在程子高亢的歌声中落幕:“血很热,你爱我,永远属于我!”至此,我们看到一部古老的复仇悲剧,在现代演绎中落实于爱的土壤,而“爱”的这条戏剧线在程婴接过那个命运襁褓时已然生成,“它比仇恨更古老,比正义更温暖”。
一部获得良好口碑的戏剧作品,离不开高品质的艺术呈现。在这部精心制作的音乐剧《赵氏孤儿》里,我们看到徐俊导演的艺术观念越来越成熟;看到郑棋元、徐均朔、方书剑等华语音乐剧演员闪耀出熠熠星光;也看到了通力合作、相互成就的团队精神。然而,我更感佩的是当代艺术家对古老文本的接受改造能力,它使得这部剧有如“一轮睁开眼睛的月亮”,向未被照亮的角落投射出清澈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