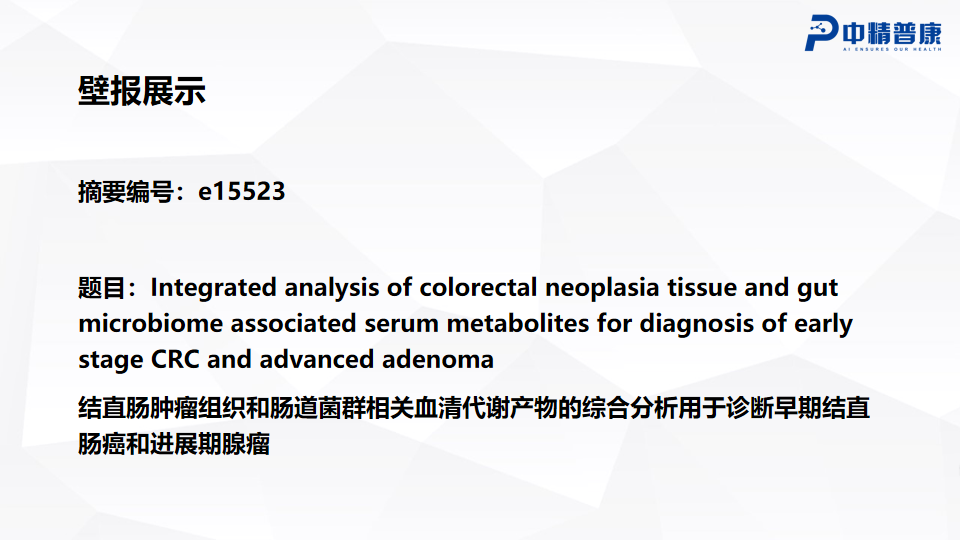话剧《红楼梦》:以四季叙事重构宝黛悲情与曹雪芹的苍凉
在舞台中央缓缓打开的三面巨大“白墙”前,红色边框,把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人物一个个框进来,白与红,也延伸到他们的服饰,昭示了基调和变奏的主题。
这是话剧《红楼梦》六个小时的全本演出。剧场外,已是秋天时节,暑气还未尽退;剧场内,春夏的“风月繁华”和秋冬的“食尽鸟归”,构成话本四季叙事的基本框架。
《红楼梦》的四季气象,早在清代二知道人(蔡家琬)的随笔《红楼梦说梦》中,已有明确的揭示,他说:
《红楼梦》有四时气象,前数卷铺叙王谢门庭,安常处顺,梦中之春也。省亲一事,备极奢华,如树之秀而繁阴葱茏可悦,梦之夏也。及通灵失玉,两府查抄,如一夜严霜,万木摧落,秋之为梦,岂不悲哉!贾媪终养,宝玉逃禅,其家之瑟缩愁惨,直如冻暮光景,是《红楼》之残梦耳。
而当代学者裘新江、梅新林、张倩等,结合了西方原型批评家弗莱《批评的剖析》中有关叙述程式的四季模式,深入探讨了《红楼梦》的四季意象结构或者四季叙事问题。不过二知道人也好,当代学者也好,他们在谈及《红楼梦》的四季叙事时,基本是从小说本身的时间向量中来进行情节分割的。而这种对直线向前发展的梳理,在话剧中被重构了。
因为四季本质上是轮回的,所以,在冬天雪地而不是漫天春光里,以哀乐中年的贾政而不是年轻的宝玉跪拜为序幕,开始人生的反思,给这种四季叙事增加了叙事的也是心灵隐喻的空间性复沓、回环和对比的意味。
这种回环和隐喻,既归拢了事件,如金钏投井、如宝玉挨打,也凸显了人物的心理感觉,让画外音出现的夏天蝉噪声,变得刺耳欲聋,让人无法忍受,同时也重置了情节,比如著名的“黛玉葬花”连同她的葬花吟放在了宝玉挨打之后,成为春夏与秋冬话剧上下本的过渡。虽然在小说中,“黛玉葬花”的情节是在宝玉挨打之前,但1940年代吴天改编的话剧《红楼梦》和1960年代徐进改编的越剧《红楼梦》,都是把“葬花”置于宝玉挨打后,特别是越剧《红楼梦》,其对这一情节的反复渲染,成为整个剧中的情节高潮。这也曾经引起有些学者不满,认为在宝玉和黛玉达成充分理解后,仍然会有黛玉误会宝玉发生悲悲戚戚的葬花举动和葬花词的咏叹,是曲解了他们的情感发展历程,也是把春末而不是夏末的季节搞错了。其实,这里的关键是,放在话剧四季整体结构中来理解,则在强调,一如自然万物凋零的规律无法改变,黛玉的葬花举动和葬花吟,已经超越了个人恩怨,是对女性整体不幸命运的悲悯。而这种整体意义的悲悯,又是跟此前舞台上展现女孩成立诗社谈诗论画的唯美风格联系在一起的。
从舞台效果看,笔者最欣赏的是笼罩在四季整体框架中的黛玉形象处理展现的四阶段:春天,黛玉进府,见到宝玉那种春心萌动;夏天,因为宝玉挨打事件,她的关切和宝玉反过来为她担心而送她旧手帕安慰她,让她写下真正的情诗,并引发了通体燃烧的夏热感;秋天,她在婚姻的绝望中,内心的希望和自然万物一起凋零;冬天,取暖的炭火只能用来焚烧她的情诗和一颗绝望的心,随着她离去,她把爱意深藏在了雪白的大地背后。总体看,这四个环节,编导都发挥出相当的创意。比如黛玉进府,是让薛宝钗进府紧随其后。在清代仲振奎改编的昆曲《红楼梦》中,薛宝钗也是和黛玉接踵而至的,不过在仲振奎的剧中,老祖宗还特意拉着宝钗去见林黛玉,说是“你们也见一见,以后总要常在一堆的”,其对两位女角进府的归并处理,似乎是为了减少另起头绪。但是在话剧中,当通报说薛宝钗也来时,贾府中所有的人都出场去迎接,把黛玉一下子冷落在舞台中央,这种强烈的对比感,使得春夏秋冬四个段落也有了内在肌理不全一致的错综感。而在接下来三段落中,无论是黛玉题诗有宝玉与之直接面对,让情感激荡得更灼人,还是咏叹黛玉葬花时,让原本洁白装束的她套上一袭红色长裾,缓缓曳地而过,或者失魂落魄的黛玉与宝钗披上红盖头的当面对比,都把情感烘托得十分强烈。
当然,如果四季叙事意味着必然的轮回,那么开头贾政在雪地里的拜别,倒应该在结尾时,由贾宝玉的雪地拜别来呼应。现在感觉是,开头很精致,结尾却有点潦草,基本通过画外音处理了元妃去世和贾府被抄。一恍惚间,演员已经上台谢幕,笔者当时都没意识到这已经终场了。这样的仓促,似乎跟戛然而止的余音绕梁,还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这本是可以在四季叙事的总框架中得到有效处理。
四季叙事之所以能够重构《红楼梦》情节而没有太多违和感,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小说构想大观园的命意本质,这是以暂时隔离开的社会礼仪和制度约束,让贾府中的大观园获得了相对理想的自然属性。这样,舞美、道具和服饰在极为简约中追求大道至简的风格,其贴近自然,也就有了理据性。从这个意义看,有些细节的处理还尚待斟酌。比如宝黛共读《西厢记》和湘云醉卧芍药花下,或坐或卧的,居然都不是野外石头而是红漆椅子等道具,这就不是简单的违背小说情节的问题。宝黛共读不被正统认可的《西厢记》,其阅读兴趣是听从心灵的自然召唤,当戏文中出现“落红成阵”的词语时,野外的花瓣也正飘落到他们的身上,这样的和谐感,跟湘云醉酒后彻底放松自己,直接躺平在野外的芍药花下青石板上,有着同样的自洽效果。在这里,人工家具的安置,哪怕再简单,也有着跟自然无法协调的冲突。
只有当王夫人亲自安排抄检大观园、驱逐晴雯等人时,冲突才从大观园外部实实在在地延伸进来,大观园相对理想的自然世界成了碎落一地的美梦。不过在话剧中,晴雯是被两个粗壮男人而不是仆妇等架出大观园,还是感觉突兀。尽管从舞台效果看,这代表了难以抗拒的强力,但细细想来,当王夫人代表刻板的社会礼制和世俗规范率领众人扫荡大观园时,他们自身不会违背礼制而让几个粗壮男仆混杂其间的。
曾经,我们把忠实于原著视为改编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比如1950年代,赵清阁改编的话剧《贾宝玉与林黛玉》就是这么自我期许并努力实践的,这当然值得褒扬。但是站在现代人立场,通过艺术改编乃至再创造,从而和原作建立一种对话关系,更具挑战意义。这是舞台艺术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1920年代,厦大学生陈梦韶等改编《红楼梦》为十四幕话剧《绛洞花主》,其中第十幕“反抗”,专门写庄主乌进孝等约来焦大、柳五儿等控诉贾府的罪恶,商议如何反抗他们的剥削,鲁迅为此写的“小引”,就是在为《红楼梦》改写成这样的社会问题剧进行辩护,认为《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写成社会剧自无不可。而当此次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用自然四季来重构《红楼梦》叙事框架时,大自然的四季轮回与人的自然感情流淌深深契合,也成了翻转小说的因子,并启发了编导力图把人的潜在情感召唤出来。于是我们看到,当赵姨娘带着怨恨情绪来送别远嫁的探春时,探春临别时把憋了很久的一声“娘”叫出来,让赵姨娘手足无措而感情失控,也让观众心头为之一震。这种对小说的再创造,也许有人会反对,但焉知不是激发小说进入新时代的一种活力?詹丹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标签: